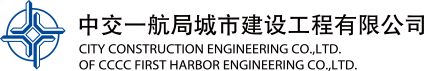我身后的那座“大山”
我家的房后有一座大山,小时候最喜欢爬山、摘野果,我那点自然常识基本上都是在上山摘果解馋的山路上获得的,大山里什么都有,能满足我的各种精神和物质需求,小时候我甚至产生了大山无所不有、无所不能的幼稚想法。

1998年以前,父亲在县城里农机厂上班。在单位宿舍的院子里玩耍,听到最多的话就是叔叔伯伯们对他说,“小龚,今天能不能加个点把这批铁皮剪完?”“这个机械的图纸我不知道怎么画才好,你帮我看看?”“我屋里的灯坏了,你有时间帮我去修一下吧?”……对于这样的事,他总是笑容可掬地一口应下来。那段时间里,我每每在外边玩耍回来,无论多晚经过大门旁边那个昏暗的仓库,都能看到他瘦弱的身躯蹲在那里敲敲打打,直到很晚才回来。
他对我却向来少言寡语,儿时记忆里,他对我说话的次数甚至都没有对厂里的同事露出笑容的次数多,这种疏远一直持续到我远离家乡,去长沙读大学的时候。

2011年我刚读大一,春节一过完我就打算返校。我需要花费11小时,翻过房后那座大山,才能到达学校。临行前一晚,我打电话对父亲说,“明天返校,我自己坐车去长沙。”我故意把“自己”二字说的很重,大概是猜到父亲必定不会送我,有点与他置气的意思。果然,他顿了一下,轻描淡写地说了4个字:“注意安全”。
出发当天,我拖着行李头也不回地坐上了赶往火车站的班车。晚上十点半,迟了半个小时的火车终于来了,但面对塞的满满当当的火车以及重重的行李,我终究因为个子瘦小被蜂拥而至的人流挤在了火车门外。凛冽的寒风如刀割,吹散了我的逻辑思维,我下意识地拨通了父亲的电话。“你出来,我在车站门口。”电话那头的声音沉稳而有力。听到这话我瞬间愕然,不知怎地声音突然哽咽了起来,“好,我,我知道了。”
走出车站,我便一眼看到了父亲,他见到我,一把接过行李,转头往车站对面的马路走去,我跟在后面看着他瘦弱的身体往左微倾,右手拎着重重的行李显得有些吃力,寒风吹得他单薄的外套不停往外翻卷,路上我们俩都没有说话。过了马路他径直走到一辆面包车跟前,与一个高个子攀谈起来,我站在路边没有到跟前去,微弱的路灯照在他身上,我才注意到他耳根发红,嘴唇略紫,想必已经在这冰冷的天气里等了许久。夹杂着寒风我隐约听到他说,“春运,人多火车不好挤,之前给你预定的座位还是没定下来。”

听到这里,我突然腿根一软蹲下了身子,眼泪“哗”地涌了出来,记忆的闸门瞬间被打开:农机厂大门旁边的仓库里,无论我多晚回去都亮起的昏暗灯光;小学春游时半道书包里莫名多出的零食;高中晚自习回家拥挤的楼道里,始终空出的恰好能放下我自行车的位置;离家200公里外冰天雪地里突然出现的身影……此时短暂的时间里我无法想象在我和他疏远的这些年里,他默默站在我的身后,对我隐藏了多少辛酸和希望,又隐藏了多少苦涩和甘甜。
车开了,我从后视镜看到他的身影越来越模糊直至看不到,这时候我的手机响了,是他发来的短信,“到了知会我。凡事别怕,有我在你身后。”看到这,我的眼泪又止不住地流下来。
从那以后每次回家去后山散步,父亲总会一同前往,一路上讲了很多他和大山的事情,现在我觉得“大山”确实无所不能,解我万忧,给我面对一切困难的无尽勇气。